那一段日子
陳智思先生(胰臟癌病人照顧者)
訪問:王榮珍女士
資料整理:穆斐文女士
廖莉莉女士


簡介:
作為癌症病人主要照顧者會面對很大的壓力:如何為病人尋找最好的治療、作最好的決定、同時亦要充當所有家庭成員溝通的橋樑。在這篇訪問中陳智思先生和我們分享他照顧患上胰臟癌媽媽的心路歷程,並且和我們探討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第一部份——攜手走過治療路程
第二部份——我和媽媽的關係
第三部份——另類治療的問題
第四部份——分離的傷痛
第五部份——如何照顧好爸爸
第六部份——陪伴、了解和修和
第七部份——生死教育
第一部份——攜手走過治療路程
王:Bernard 很感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我知道伯母是在數年前患胰臟癌過世的,而你是她的照顧者。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作為一個兒子照顧媽媽的心路歴程。
陳: 我媽媽是於2014年發現有胰臟癌的,發現的時候是早期。她是去看皮膚科醫生的時候,醫生發現在她右腿有一些硬塊,繼而進行各類檢查確診是早期胰臟癌。之後媽媽進行胰臟十二指腸切除手術( Whipple Operation),又再做化療,最後在2016年離世,前後大約是兩年多。
王: 那你是怎樣陪媽媽走過治療之路呢?
陳: 其實我多年來和醫生打慣交道,我從18歲開始便確診罕見的血管收縮病症高安氏動脈炎,前後做過多次手術包括兩次腎臟手術,其中最大一次做完需要臥床休息兩個月。所以我較一般人能夠接受疾病和懂得冷靜處理。 但是當我面對自己媽媽患癌時,反應是完全不是這樣。
在媽媽確診是胰臟癌之後,她的外科醫生和癌症專科醫生均認為她需要儘快做一個名為 Whipple 的手術。我想我當時是太overwhelmed 了,沒有太多猶豫,只想媽媽儘快得到治療,所以與家人初步商量過後便答應醫生立即進行手術。 而媽媽也很快便接受了這個手術。 可是在做完手術之後我將這件事情告訴我的朋友,他們當中有些持不同意見,說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手術,在決定之前應詳加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包括風險、手術如不成功的後果等等,有數個更問我有沒有seek second opinion。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有點迷惑, 我越聽就越覺得擔心,並思考做這個手術是否真的正確? 對媽媽是否最好呢? 我忽然覺得好大壓力、好困擾。 若將來手術有甚麼問題, 我怎麼這樣衝動就幫媽媽答應做這個手術呢? 如果將來有什麼事,我怎麼能擔當得起呢?
幸而手術最後是成功的,所以我放下心頭大石。雖然如此,有時我還是會問自己當初的決定是否太倉猝了,因為這是非常against my character。 可能這就是大家常說的:「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王: 面對這麼重要的決定,照顧者是應該多用一點時間去尋找資料和詳細思考,確保將來的決定是完全穩妥而不會後悔的。
陳: 同時我亦想帶出另一個訊息,就是很多時在照顧一個病人時,家庭都會找一個成員作為「主要」的照顧者(primary carer),統籌各方面的事宜和必要時為病人作出選擇(特別是有緊急狀況時)。 而很多時這位成員都承受很大壓力。
這個時候,作為其他家人,應該支持他非常重要的決定,如有什麼意見,各家庭成員應該在未做決定之前提出,之後就算決定最終沒有帶來理想的後果,大家都不應該埋怨, 而是一起承擔,否則那會令主要照顧者非常難受, 更會影響家庭關係。
在面對至愛親人患上癌症的事上,一家人的團結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慶幸我的家人都對我非常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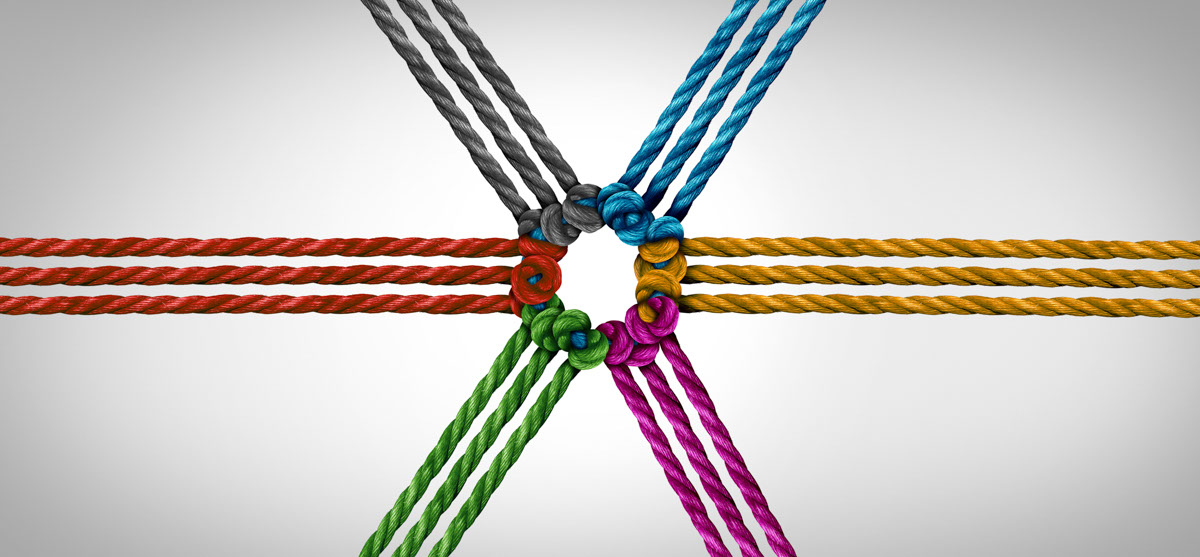
第二部份——我和媽媽的關係
陳:我是生長於一個潮州家庭,我媽媽就是典型的家庭主婦,對子女管教非常之嚴謹, 同時性格非常強。 我媽媽患上癌症之後,不幸爸爸又因為有一些病毒入侵身體而導致頗嚴重的健康問題。 所以一家人承受的壓力都非常之大。 媽媽一生人覺得她最大的責任就是要照顧爸爸,所以她雖然患上癌症,而且在治療期間也一定是面對不少痛苦,但是她還是非常努力地表現冷靜,繼續正常生活,希望大家不因為擔心她而生活受到影響。
但是在這平靜的表面下,我能察覺到她的恐懼和焦慮。特別是很多時朋友熱心的向她提供各種另類治療方案,她在嘗試之後發覺沒有用,那種失落令她格外難受。

第三部份——另類治療的問題
王: 我知道伯母在接受正統西醫治療期間也試過一些另類治療。
這也是照顧者常常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應不應該支持病人去嘗試一些沒有科學根據的治療呢? 感覺上是沒有用的,但又擔心萬一真的有些用,我便會對不起病人。
陳:對的。 當時我也面對這個問題,覺得難以決定。
其實我年青時作為一個病人,也有很多好心人向我提議這樣那樣的另類治療方案,什麼神醫、靈藥等等,令我非常迷惑和混亂, 最後我決定完全回絕這些建議。
但是到我媽媽遇上這樣的情況,我卻沒有勇氣作出同樣的決定。 原來一個人要為自己做決定是比較容易的,但為別人做決定則是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王:那伯母最終有沒有嘗試這些另類治療呢?
陳:有的。最主要的一次是我們到了德國接受一種另類治療,在那裏足足逗留了兩個多月。 你問我這個治療有沒有用,我感覺是沒有用的。
王: 這個治療有沒有為伯母帶來任何好處(例如是心理上)? 又或是帶來任何壞處? 我的意思是有沒有帶來一些格外的痛苦? 同時伯母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
陳:我現在也不太記得清楚,好像是牽涉到熱力照射,將一些液體注入她腹腔內,我相信是有一些痛苦的。
我想媽媽實在是太希望延長生命去繼續照顧我爸爸,所以她還是希望嘗試。
王: 我曾請教過一些醫生關於另類治療的看法,他們建議作為照顧者,我們應該為病人冷靜的搜集一些客觀資料,作出 evidence based 及詳細的評估。 損失金錢還不是最重要的,最擔心的是為此拖延了需要/適時的治療。
但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病人自己的意願。 如果病人堅持接受一些治療,就算我們作為照顧者不同意的話,是不是都應該尊重他的意願呢? 因為畢竟 at stake 的都是他的生命。在英文來說是 ‘go along’。

第四部份——分離的傷痛
王:我了解伯母在治療兩年多之後終於離世。別離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請問當時你是如何面對呢?
陳:我媽媽離世之前,已經病了很久,到最後期甚至要注射藥物止痛,注射了兩天嗎啡,在心理上我已作好準備,當她離開那一刻,我覺得還是ok的,只希望她不再辛苦。
但是最痛苦的感覺卻是在之後一層一層的浮現。首先我要負責做各樣手續,例如在需要的情況之下確認遺體、辦理死亡證、安排、尋找墓地等等。由於我之前完全沒有類似經歷,所以便一次又一次感到震驚和創痛。第一次是需要從私家醫院陪同媽媽的遺體由病房到樓下上一架專車運送到殮房。當我看著媽媽被送上車離我而去時,途中我注視着棺木,那一刻我確確切切的意識到媽媽真的是離開我了、是永遠不在了! 那令我極度迷惘和傷心。
王:我的分析是我們一直知道親人即將會離去,所以心理上重複又重複的叫自己作好準備,到時要勇敢面對。 這就是為什麼在伯母離世那一刻,你還是覺得OK。又或者是在那一刻,你精神上可能有些英文叫 delirious 的狀態,人有些麻木而腦部又好像不能 process 資料。 但是在之後當震央慢慢到達腦部,便感到強烈的刺痛。
同時如果照顧者從來沒有面對過親人離世的經驗,則震盪會更強烈。再加上在準備後事上從來沒有任何經驗,每一個步驟都像是用刀切在剛愈合的傷口。
我媽媽離世的時候,我一方面很想親手為她做每一件「後事」,例如是辦死亡證、選擇壽衣/棺木等,但同時又覺得非常害怕和痛苦。所以我當時去請教過一個專家朋友,他告訴我親人離世後,照顧者是不是親自去處理後事,根本是不重要的。 如果他情緒不能承受的話,為何要那麼殘忍逼他去做,找其他人代辦便可。 例如是照顧者的配偶又或是死黨。 換句話說就是一些和死者close 的人,但又不是最close最close 的人。
陳:對的。每一次辦手續我都覺得很痛苦,真是 sequence of traumas —令我意識到she is really gone;she is really really gone。
你說有需要時不用由亡者最親的人去辦理後事是個不錯的選擇, 這個建議非常之好。如果將來我有朋友遇上這樣的情況,我也會告訴他這個選擇。

第五部份——如何照顧好爸爸
陳:另外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媽媽離世之後,我們非常擔心爸爸如何能承受這樣大的打擊。
媽媽離開之前,曾經殷切吩咐我們所有兄弟姊妹,她走了之後我們要好好照顧爸爸。 所以我們便協議每天晚上都要有人回去陪爸爸吃晚飯,不要令他感到孤寂。
王: 是啊!一個人如果突然失去了相處數十載的配偶,那個衝擊真是非常的大! 特別是男士,由於一直都是由太太一手一腳的照顧,太太離去之後都很徬徨,要努力尋找一個新的模式去解決生活的需要。
[註:請參考「如何照顧失去配偶的父親或母親」章節]

第六部份——陪伴、了解和修和
王:Bernard,今天我們作了這麼詳細的討論,如果是時光倒流,你有機會做得更好,那麼你覺得你在照顧你媽媽的過程中有什麼需要改善呢?
陳:正如我告訴你,我媽媽一直是個強者,所以在她患病期間,她沒有要求我們常常陪伴她,怕影響我們的生活。 而我雖然替她安排實際上需要,例如看什麼醫生、住什麼醫院、什麼人陪她去覆診等等,但是我自己並沒有抽太多時間去親自陪伴她,例如陪她去做化療。 因為當時我覺得我已做了最好的安排,盡了做兒子的責任。 但是現在回想,我實在是應該用多一些時間陪伴她的! I have taken her a bit for granted。 I should have done it even though she has not asked for it.
另外,要照顧自己最親的人面對患疾實在是一個很磨人的經驗,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那也是人生中一個極罕有和寶貴的機會,令大家有深切的溝通和了解。
我記得我年青的時候非常害怕媽媽,因為她是一個極之嚴格的傳統媽媽, 典型的「虎媽」,對我有很多要求,令我有很大壓力。 在我18歲那年,由於在美國要做一個非常大的手術,媽媽便要飛過來陪我,更要在我家住兩個月,我當時擔心死了,就是我怎麼捱過這段日子。 後來她真的來了,雖然在生活細節上我們亦要有些磨合,但在那段日子我們都能坦誠講出心裏的感受——我告訴她我感到的壓力;而她則告訴我她為何認為她管教我的方法是最好的。 雖然我不完全認同她的想法,但到底也對她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亦開始嘗試去尊重她的想法。
所以我覺得如果家人之中心裏有芥蒂,到其中一方患病的時候,大家便應放下歧見,坦誠的告訴對方自己的想法,並希望得到和解,就是reconciliation。
王:對啊! 如果大家到最後都不能和解,這是多麼令人遺憾的事呢!
[註:請參考「五道人生」章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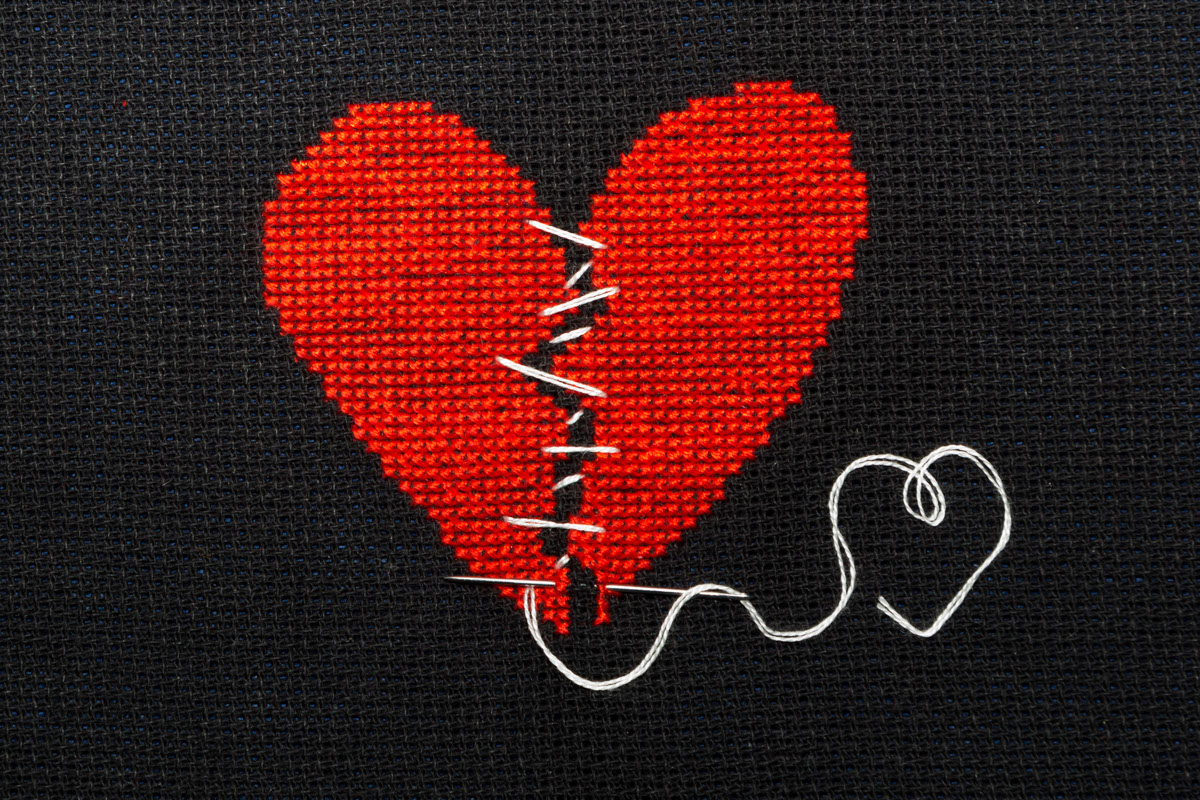
第七部份——生死教育
陳:另外有種處境是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的。
這就是當我和媽媽最後相處的時候,其實大家都知道病情已經是非常嚴重,那麼作為照顧者的我是應該怎樣安慰她? 說樂觀的話又覺得大家都不相信;但說出真相和坦誠的話又好像非常冷酷。
從這裏我就不禁有一些慨嘆——就是為什麼人在beginning of life 的角度花費那麼多的氣力(去為子女籌謀他們的教育),但對於 end of life 那麼重要的課題,卻完全不肯去花費心思。 可能是由於我們中國人覺得這是一個忌諱,但是我深深認為我們如何處理父母的離世,將會影響我們子女將來面對死亡的態度。
王:絕對同意! 我的朋友謝醫生多年前在香港成立了一個生死教育會,就是希望大家對這個課題多一些認識,為自己多作一些準備。我去參加過他們主辦的講座,發人深省!
一句俗語說「船到橋頭自然直」,那是對的。 但是如果沒有準備、橋是破破爛爛的,那麼用者雖然最後能上到船,但是在奔走期間也會跌倒受傷。 所以還是不如早一點作準備較好。
Bernard ,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你替我們分享你的心路歷程!
(於2020年12月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