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日子
陈智思先生(胰脏癌病人照顾者)
访问:王荣珍女士
资料整理:穆斐文女士
廖莉莉女士


简介:
作为癌症病人主要照顾者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如何为病人寻找最好的治疗、作最好的决定、同时亦要充当所有家庭成员沟通的桥樑。在这篇访问中陈智思先生和我们分享他照顾患上胰脏癌妈妈的心路历程,并且和我们探讨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第一部份——携手走过治疗路程
第二部份——我和妈妈的关係
第三部份——另类治疗的问题
第四部份——分离的伤痛
第五部份——如何照顾好爸爸
第六部份——陪伴、了解和修和
第七部份——生死教育
第一部份——携手走过治疗路程
王:Bernard 很感谢你接受我的访问。
我知道伯母是在数年前患胰脏癌过世的,而你是她的照顾者。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个儿子照顾妈妈的心路歴程。
陈: 我妈妈是於2014年发现有胰脏癌的,发现的时候是早期。她是去看皮肤科医生的时候,医生发现在她右腿有一些硬块,继而进行各类检查确诊是早期胰脏癌。之後妈妈进行胰脏十二指肠切除手术( Whipple Operation),又再做化疗,最後在2016年离世,前後大约是两年多。
王: 那你是怎样陪妈妈走过治疗之路呢?
陈: 其实我多年来和医生打惯交道,我从18岁开始便确诊罕见的血管收缩病症高安氏动脉炎,前後做过多次手术包括两次肾脏手术,其中最大一次做完需要卧床休息两个月。所以我较一般人能够接受疾病和懂得冷静处理。 但是当我面对自己妈妈患癌时,反应是完全不是这样。
在妈妈确诊是胰脏癌之後,她的外科医生和癌症专科医生均认为她需要儘快做一个名为 Whipple 的手术。我想我当时是太overwhelmed 了,没有太多犹豫,只想妈妈儘快得到治疗,所以与家人初步商量过後便答应医生立即进行手术。 而妈妈也很快便接受了这个手术。 可是在做完手术之後我将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朋友,他们当中有些持不同意见,说这是一个非常複杂的手术,在决定之前应详加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包括风险、手术如不成功的後果等等,有数个更问我有没有seek second opinion。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有点迷惑, 我越听就越觉得担心,并思考做这个手术是否真的正确? 对妈妈是否最好呢? 我忽然觉得好大压力、好困扰。 若将来手术有甚麽问题, 我怎麽这样衝动就帮妈妈答应做这个手术呢? 如果将来有什麽事,我怎麽能担当得起呢?
幸而手术最後是成功的,所以我放下心头大石。虽然如此,有时我还是会问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太仓猝了,因为这是非常against my character。 可能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王: 面对这麽重要的决定,照顾者是应该多用一点时间去寻找资料和详细思考,确保将来的决定是完全稳妥而不会後悔的。
陈: 同时我亦想带出另一个讯息,就是很多时在照顾一个病人时,家庭都会找一个成员作为「主要」的照顾者(primary carer),统筹各方面的事宜和必要时为病人作出选择(特别是有紧急状况时)。 而很多时这位成员都承受很大压力。
这个时候,作为其他家人,应该支持他非常重要的决定,如有什麽意见,各家庭成员应该在未做决定之前提出,之後就算决定最终没有带来理想的後果,大家都不应该埋怨, 而是一起承担,否则那会令主要照顾者非常难受, 更会影响家庭关係。
在面对至爱亲人患上癌症的事上,一家人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庆幸我的家人都对我非常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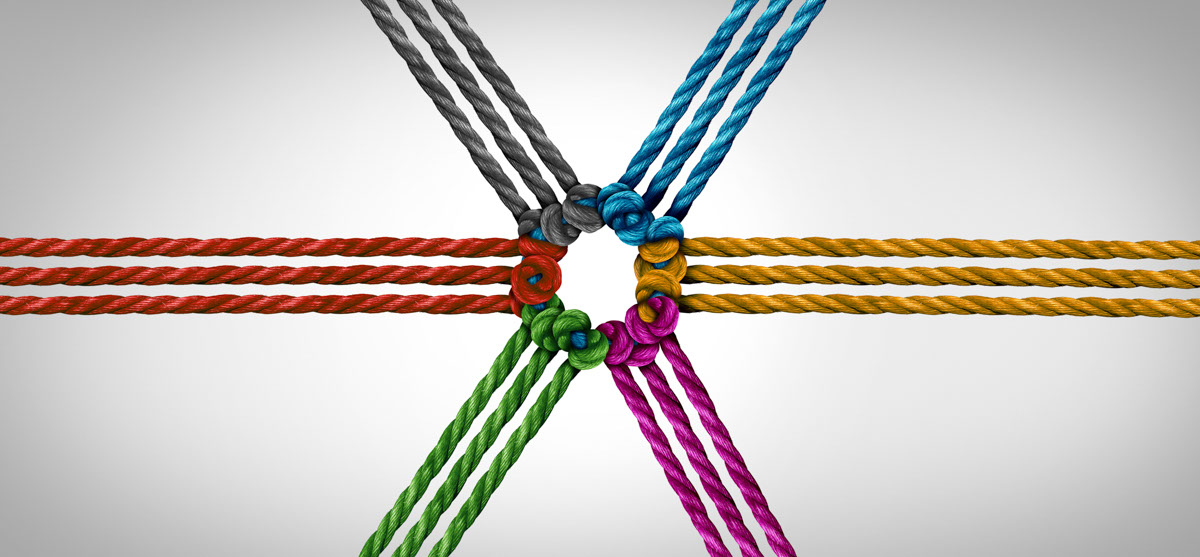
第二部份——我和妈妈的关係
陈:我是生长於一个潮州家庭,我妈妈就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对子女管教非常之严谨, 同时性格非常强。 我妈妈患上癌症之後,不幸爸爸又因为有一些病毒入侵身体而导致颇严重的健康问题。 所以一家人承受的压力都非常之大。 妈妈一生人觉得她最大的责任就是要照顾爸爸,所以她虽然患上癌症,而且在治疗期间也一定是面对不少痛苦,但是她还是非常努力地表现冷静,继续正常生活,希望大家不因为担心她而生活受到影响。
但是在这平静的表面下,我能察觉到她的恐惧和焦虑。特别是很多时朋友热心的向她提供各种另类治疗方案,她在尝试之後发觉没有用,那种失落令她格外难受。

第三部份——另类治疗的问题
王: 我知道伯母在接受正统西医治疗期间也试过一些另类治疗。
这也是照顾者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支持病人去尝试一些没有科学根据的治疗呢? 感觉上是没有用的,但又担心万一真的有些用,我便会对不起病人。
陈:对的。 当时我也面对这个问题,觉得难以决定。
其实我年青时作为一个病人,也有很多好心人向我提议这样那样的另类治疗方案,什麽神医、灵药等等,令我非常迷惑和混乱, 最後我决定完全回绝这些建议。
但是到我妈妈遇上这样的情况,我却没有勇气作出同样的决定。 原来一个人要为自己做决定是比较容易的,但为别人做决定则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王:那伯母最终有没有尝试这些另类治疗呢?
陈:有的。最主要的一次是我们到了德国接受一种另类治疗,在那裏足足逗留了两个多月。 你问我这个治疗有没有用,我感觉是没有用的。
王: 这个治疗有没有为伯母带来任何好处(例如是心理上)? 又或是带来任何坏处? 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带来一些格外的痛苦? 同时伯母自己的想法又是如何?
陈:我现在也不太记得清楚,好像是牵涉到热力照射,将一些液体注入她腹腔内,我相信是有一些痛苦的。
我想妈妈实在是太希望延长生命去继续照顾我爸爸,所以她还是希望尝试。
王: 我曾请教过一些医生关於另类治疗的看法,他们建议作为照顾者,我们应该为病人冷静的搜集一些客观资料,作出 evidence based 及详细的评估。 损失金钱还不是最重要的,最担心的是为此拖延了需要/适时的治疗。
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病人自己的意愿。 如果病人坚持接受一些治疗,就算我们作为照顾者不同意的话,是不是都应该尊重他的意愿呢? 因为毕竟 at stake 的都是他的生命。在英文来说是 ‘go along’。

第四部份——分离的伤痛
王:我了解伯母在治疗两年多之後终於离世。别离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请问当时你是如何面对呢?
陈:我妈妈离世之前,已经病了很久,到最後期甚至要注射药物止痛,注射了两天吗啡,在心理上我已作好準备,当她离开那一刻,我觉得还是ok的,只希望她不再辛苦。
但是最痛苦的感觉却是在之後一层一层的浮现。首先我要负责做各样手续,例如在需要的情况之下确认遗体、办理死亡證、安排、寻找墓地等等。由於我之前完全没有类似经历,所以便一次又一次感到震惊和创痛。第一次是需要从私家医院陪同妈妈的遗体由病房到楼下上一架专车运送到殓房。当我看著妈妈被送上车离我而去时,途中我注视着棺木,那一刻我确确切切的意识到妈妈真的是离开我了、是永远不在了! 那令我极度迷惘和伤心。
王:我的分析是我们一直知道亲人即将会离去,所以心理上重複又重複的叫自己作好準备,到时要勇敢面对。 这就是为什麽在伯母离世那一刻,你还是觉得OK。又或者是在那一刻,你精神上可能有些英文叫 delirious 的状态,人有些麻木而脑部又好像不能 process 资料。 但是在之後当震央慢慢到达脑部,便感到强烈的刺痛。
同时如果照顾者从来没有面对过亲人离世的经验,则震盪会更强烈。再加上在準备後事上从来没有任何经验,每一个步骤都像是用刀切在刚愈合的伤口。
我妈妈离世的时候,我一方面很想亲手为她做每一件「後事」,例如是办死亡證、选择寿衣/棺木等,但同时又觉得非常害怕和痛苦。所以我当时去请教过一个专家朋友,他告诉我亲人离世後,照顾者是不是亲自去处理後事,根本是不重要的。 如果他情绪不能承受的话,为何要那麽残忍逼他去做,找其他人代办便可。 例如是照顾者的配偶又或是死党。 换句话说就是一些和死者close 的人,但又不是最close最close 的人。
陈:对的。每一次办手续我都觉得很痛苦,真是 sequence of traumas —令我意识到she is really gone;she is really really gone。
你说有需要时不用由亡者最亲的人去办理後事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建议非常之好。如果将来我有朋友遇上这样的情况,我也会告诉他这个选择。

第五部份——如何照顾好爸爸
陈: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妈妈离世之後,我们非常担心爸爸如何能承受这样大的打击。
妈妈离开之前,曾经殷切吩咐我们所有兄弟姊妹,她走了之後我们要好好照顾爸爸。 所以我们便协议每天晚上都要有人回去陪爸爸吃晚饭,不要令他感到孤寂。
王: 是啊!一个人如果突然失去了相处数十载的配偶,那个衝击真是非常的大! 特别是男士,由於一直都是由太太一手一脚的照顾,太太离去之後都很徬徨,要努力寻找一个新的模式去解决生活的需要。
[註:请参考「如何照顾失去配偶的父亲或母亲」章节]

第六部份——陪伴、了解和修和
王:Bernard,今天我们作了这麽详细的讨论,如果是时光倒流,你有机会做得更好,那麽你觉得你在照顾你妈妈的过程中有什麽需要改善呢?
陈:正如我告诉你,我妈妈一直是个强者,所以在她患病期间,她没有要求我们常常陪伴她,怕影响我们的生活。 而我虽然替她安排实际上需要,例如看什麽医生、住什麽医院、什麽人陪她去覆诊等等,但是我自己并没有抽太多时间去亲自陪伴她,例如陪她去做化疗。 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已做了最好的安排,尽了做儿子的责任。 但是现在回想,我实在是应该用多一些时间陪伴她的! I have taken her a bit for granted。 I should have done it even though she has not asked for it.
另外,要照顾自己最亲的人面对患疾实在是一个很磨人的经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那也是人生中一个极罕有和宝贵的机会,令大家有深切的沟通和了解。
我记得我年青的时候非常害怕妈妈,因为她是一个极之严格的传统妈妈, 典型的「虎妈」,对我有很多要求,令我有很大压力。 在我18岁那年,由於在美国要做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妈妈便要飞过来陪我,更要在我家住两个月,我当时担心死了,就是我怎麽捱过这段日子。 後来她真的来了,虽然在生活细节上我们亦要有些磨合,但在那段日子我们都能坦诚讲出心裏的感受——我告诉她我感到的压力;而她则告诉我她为何认为她管教我的方法是最好的。 虽然我不完全认同她的想法,但到底也对她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亦开始尝试去尊重她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如果家人之中心裏有芥蒂,到其中一方患病的时候,大家便应放下歧见,坦诚的告诉对方自己的想法,并希望得到和解,就是reconciliation。
王:对啊! 如果大家到最後都不能和解,这是多麽令人遗憾的事呢!
[註:请参考「五道人生」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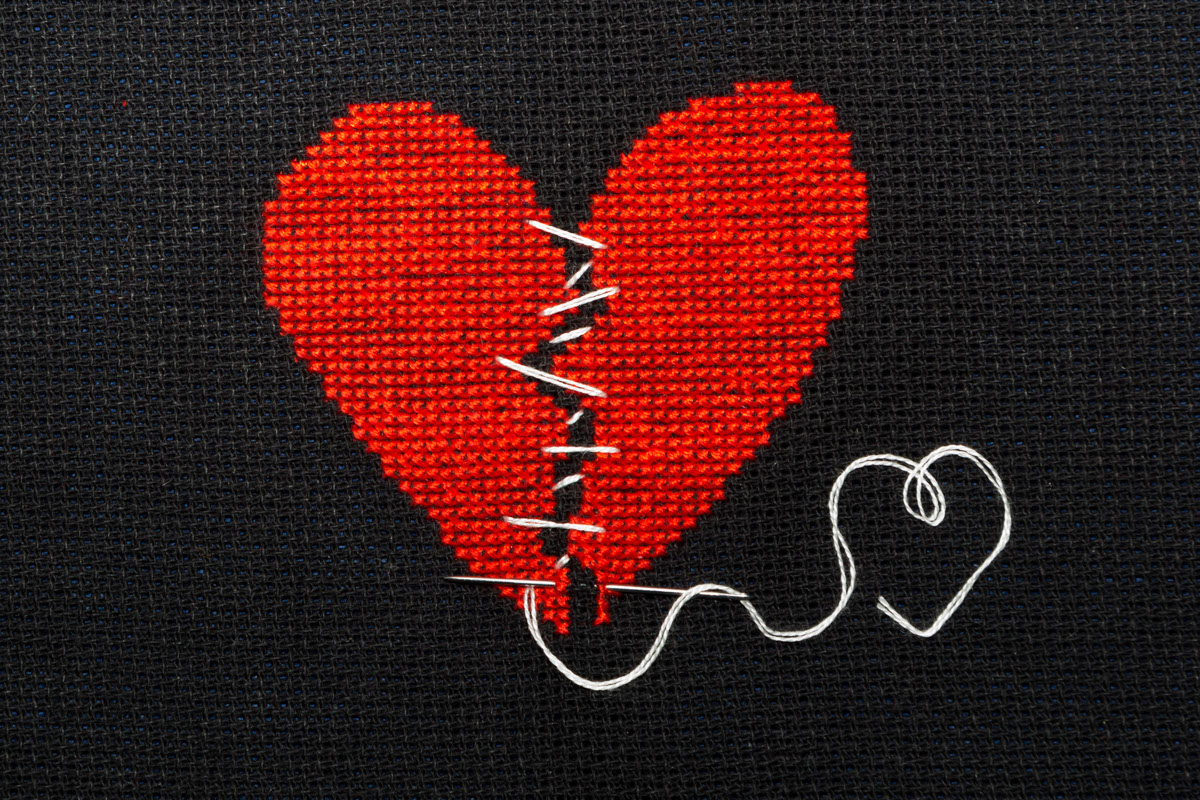
第七部份——生死教育
陈:另外有种处境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的。
这就是当我和妈妈最後相处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病情已经是非常严重,那麽作为照顾者的我是应该怎样安慰她? 说乐观的话又觉得大家都不相信;但说出真相和坦诚的话又好像非常冷酷。
从这裏我就不禁有一些慨叹——就是为什麽人在beginning of life 的角度花费那麽多的气力(去为子女筹谋他们的教育),但对於 end of life 那麽重要的课题,却完全不肯去花费心思。 可能是由於我们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忌讳,但是我深深认为我们如何处理父母的离世,将会影响我们子女将来面对死亡的态度。
王:绝对同意! 我的朋友谢医生多年前在香港成立了一个生死教育会,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个课题多一些认识,为自己多作一些準备。我去参加过他们主办的讲座,发人深省!
一句俗语说「船到桥头自然直」,那是对的。 但是如果没有準备、桥是破破烂烂的,那麽用者虽然最後能上到船,但是在奔走期间也会跌倒受伤。 所以还是不如早一点作準备较好。
Bernard ,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替我们分享你的心路历程!
(於2020年12月定稿)





